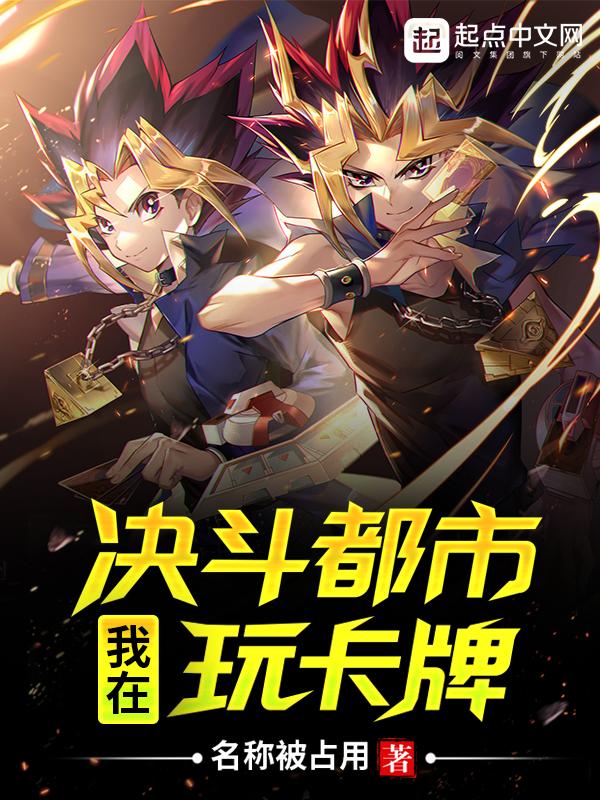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我在唐朝当国公 > 第一百一十一章 边患突起 军费之争(第1页)
第一百一十一章 边患突起 军费之争(第1页)
书房的烛火轻轻摇曳,映照着方羽凝重的脸庞。
北境云州都督府的八百里加急军报,如同沉重的石块投入平静的湖面,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涟漪。突厥部落联盟异动,袭扰边境,兵锋渐盛,边军压力骤增。
“军费,粮草,援军……”方羽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,眼神锐利。
他才刚刚接手户部不久,漕运改革初见成效,正待进一步巩固推行,这北境的烽烟就毫无预兆地燃了起来。
打仗,打的就是钱粮!这副重担,最终还是要落到他这个户部侍郎的肩上。王德忠那边,怕是又要借题发挥了。
果不其然,次日清晨的朝会,气氛格外肃杀。
李隆基端坐龙椅,面沉似水。云州都督的奏报已传阅至诸位重臣手中。
殿内一片寂静,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率先打破沉默的,正是王德忠。他手持笏板,上前一步,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渲染的沉痛与忧虑:
“陛下,北境军情紧急,突厥狼子野心不死,屡犯我边疆,杀我子民,掠我牲畜,实乃心腹大患!臣以为,当务之急,是立刻调拨大笔军费,增兵北境,给予云州都督府最大支持,务必将突厥的嚣张气焰打下去,扬我大唐国威!”
他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,冠冕堂皇,似乎全是为了国家安危着想。
然而,话锋一转,他便将矛头指向了户部,或者说,指向了方羽:
“只是……陛下,臣亦有担忧。前番推行漕运改革,虽说是为了提高效率,但耗费亦是巨大,各处疏浚河道,建造新船,官员调动安置,无不需要钱粮。如今国库……怕是有些捉襟见肘啊!这应对北境边患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军费,户部……不知方侍郎可有良策应对?”
来了!
方羽心中冷笑,面上却不动声色。
王德忠果然老辣,先大谈边患之危,再把矛头引向漕改,这是要把掏空国库的帽子扣死在我头上。更阴险的是,他借此机会鼓吹大幅增加军费,一旦朝廷采纳,这笔巨款由谁来经手,如何使用,里面的猫腻可就大了去了。他王德忠在军中并非没有势力,正好可以安插亲信,上下其手,大发国难财。
一时间,不少官员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方羽身上,有担忧,有疑虑,也有幸灾乐祸。
李显眉头紧锁,看了方羽一眼,眼神中带着询问和鼓励。
方羽上前一步,身姿挺拔,声音清晰而沉稳,响彻整个太极殿:“陛下,王相所言北境军情紧急,臣亦深以为然。然,王相言及漕运改革耗空国库,致使难以应对边患,此言,臣不敢苟同。”
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账册摘要,朗声道:“陛下请看,此乃改革前后,漕运主要线路的税收及转运成本对比。改革之后,运力提升近三成,损耗降低近两成,沿途关卡税收因货流通畅反而增加了半成!综合算来,漕运改革初期投入虽大,但其带来的长远效益已初步显现,非但未耗空国库,反而为国库开源节流,增加了不少进项!”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王德忠,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:“国库目前确实不算特别充裕,毕竟百废待兴,用钱的地方甚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应对北境边患。关键不在于盲目地投入多少钱,而在于如何将有限的钱粮,用在最关键的地方,用出最大的效果!”
“哦?”李隆基来了兴趣,身体微微前倾,“方爱卿有何高见?”
“臣以为,应对边患,非一味增兵、滥撒钱粮可解。”方羽侃侃而谈,
“其一,当务之急是巩固边防。臣建议,重点加强云州及周边几个关键隘口的防御工事。臣近日偶得一物之配方,名曰‘水泥’,此物以寻常石料烧制而成,与沙石混合,遇水则凝,坚硬逾石,且成本低廉。若用于修筑关墙、碉堡,其坚固程度远胜土石,且可大大缩短工期,节省人力物力。”
水泥?
殿内众人面面相觑,闻所未闻。
方羽继续道:“其二,提升边军战力,不在人多,而在精锐。与其盲目扩军,不如将钱粮用于改善现有边军的武器装备,提高甲胄、弓弩、战马的质量与数量。同时,建立更高效的后勤补给系统,确保粮草、药材、军械能够及时、足额送达前线,免除将士后顾之忧。”
“其三,赏罚分明,激励士气。对于作战勇猛、斩获颇丰的将士,应不吝赏赐;对于临阵脱逃、贻误战机者,严惩不贷。如此,方能使三军用命,奋勇杀敌。”
听完方羽的陈述,李隆基微微颔首,显然对方羽这套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务实之策颇感兴趣,殿内气氛也为之一变。
兵部尚书,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站了出来,瓮声瓮气地说道:“陛下,臣以为方侍郎所言,颇有见地!尤其是那‘水泥’之法,若真如其所言,能以廉价石料筑成坚逾金石的工事,对我北境边防而言,不啻于天降神助!臣请陛下,允方侍郎详述此法,并拨付少量钱粮试行,若成,则可大力推广!”